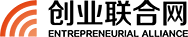年輕人開始進入廢品回收行業。
2019年,做了10年職業經理人后,985大學畢業的楊斌終于說服了父親,開始“收廢品”創業。
楊斌主要經營廢品回收中心,連接廢品回收站和廢品再回收工廠。作為“新一代”的廢品回收從業者,楊斌也探索起團隊化、規模化的作業形式,并制定廢品回收站覆蓋計劃、從源頭管理“貨源”。
同時,楊斌也開發了“易馬回收”小程序,用互聯網的新方式改造廢品回收這一產業。對于楊斌來說,“收廢品”并不是一份不光彩、上不了臺面的工作,而是自己的興趣所在、創業夢想之地,他也打算將自己的“廢品回收”版圖,從青島擴展向全國。
在楊斌的上游,95后的阿怡也在2022年進入了廢品回收行業,“當時找工作不順利,小姨又剛好在杭州收廢品,就勸我暫時可以收廢品,雖然累,但總比上班要好些。”
于是阿怡就入了廢品回收的“門”,承包了社區的一個網點,一面清理網點“廢品”,一面宣傳垃圾分類知識。
同在2022年,00后的李信也一腳跨進了廢品回收的“門”,做的是廢品回收最上游的一環——上門回收。但年輕人也有新的想法,李信所做的廢品回收也不再是“蹬著三輪車走街串巷”,而是通過用社交平臺改造“收廢品”鏈條上最原始的一環。
年輕人們紛紛入局的廢品回收行業,也叫做“再生資源行業”,雖然“冷門”,卻“悶聲賺大錢”。
在最下游的上門回收人員,一個月的收入在5000-10000元之間;再上一環的廢品回收站,收入規模主要取決于店面位置和運營能力,但一年正常也能“10萬元保底,盈利在20萬元左右”。楊斌介紹。
而到了楊斌所在的中游“回收中心”,收入的跨度更大,往往能跨越20-50萬元之間,雇傭的人越多、機器越多,收入就越高,“最上游的回收工廠,收入自然就是另一個量級了。”楊斌補充道。
根據公開數據顯示,2022年,我國廢鋼鐵、廢塑料、廢紙等十種品類再生資源回收總量約3.71億噸,回收總額超過1.31萬億元。目前,我國再生資源回收企業約9萬多家,中小型企業占主流,從業人員約1300萬人。
對于這群進入廢品回收行業的年輕人來說,雖然仍擺脫不了臟、累、苦,但也“整頓行業”,帶來了新的變化和面貌,比如更專業的人員隊伍、團隊運作,以及互聯網等新方式。
同時,也帶來了職業改觀,收獲了職業自豪感,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狀元,收廢品也是資源再回收的一環,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。”楊斌表示。
阿怡也說道,“社區里的居民不僅因為我們的宣講增加了環保意識,而且我們的存在本身,也讓廢品回收這件事更專業化了。”
誰說收廢品不能時髦呢?
年輕人“改造”廢品回收
“985畢業收廢品,那你為什么還要上大學呢?”
2009年,從某985大學畢業時,楊斌就曾向父親提出接力父親手中的廢品回收生意,從事廢品回收創業,但遭到了父親及親戚的強烈反對。
楊斌至今仍記得父親的憤怒與質疑,畢竟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,“收廢品在很多人看來,是不光彩的,上不了臺面的。”
在十年妥協之后,楊斌還是步入了這一條夢想的河流,開啟了廢品回收創業。
但年輕人進入“收廢品”行業,已經與“騎著三輪車走街串巷叫賣收廢品”的古舊印象大不相同。
做了十年經理人,楊斌對效率、規模有更多的想法,作為連接廢品回收站和廢品再回收工廠的中間環節,“轉運中心需要覆蓋更多回收站。”
楊斌也嘗試用更數據化的工具,讓“收廢品”這項大眾認知里似乎只需“用苦力”去做的工作,運轉的效率更高,制定廢品回收站覆蓋計劃,從源頭管理“貨源”。
此外,空閑的時間,他會打開自己創辦的“易馬回收”小程序,“客戶在小程序下單,我們根據時間地點匹配相應的人員和車輛。”
承包網點的阿怡上手后也發現,杭州有不少專門做資源回收業務的公司,因此在各個社區、各個區域,都設立了宣傳垃圾分類的網點。此前她以為,收廢品就是要蹬著三輪車,在臭氣熏天的垃圾堆里翻找,沒想到其實只需要進社區,就能有客戶上門。
2022年,畢業一年的00后李信,也開始嘗試用社交平臺改造“收廢品”鏈條上最原始的一環——“上門回收”。
“現在天氣熱,我只需要在抖音、小紅書等社交平臺記錄收廢品的日常生活,就能吸引到有需求的客戶,坐等生意上門。”李信表示。
李信介紹,收廢品要想掙錢,客源最為關鍵,但在過去,怎么才能收到好貨,往往要依靠積攢的人脈,加上一部分經驗,甚至少不了一些運氣“加成”,現在他在社交平臺上“吆喝”,“通過互聯網就能找到精準的意向客戶。”比起過去沿街苦等,“要輕松多了。”
除了為自己的廢品回收生意招攬貨源,建立起線上接單渠道后,主收銅鐵等金屬的李信,在接到收紙、瓶子等其他需求的客戶時,也會聯系其他對口的叔伯朋友“接單”,不知不覺成了北京收廢品的客源中轉站。
在本職工作“收廢品”之外,此前,李信還曾利用互聯網、社交平臺,和朋友一起為朋友父親的裝修生意“攬活”,搭上互聯網這一平臺之后,以前“活做完就等,做完上一單,不知道下一單在哪里”的朋友父親,現在“活多到都得排期”。
同時,年輕人進入廢品回收行業,并以互聯網等方式“整頓行業”,也把此前苦于“不要的家具白給都沒人拿”的年輕人帶入了廢品回收的“交易場”。
李信介紹,“不少年輕人打電話約上門回收,很多都不要錢,只求把家里占地的東西拉走就好。”而相比起走街串巷的回收大爺,也有不少年輕人擔心碰上“鬼秤”,轉而選擇線上邀約下單。
“從線上下單到最后拉走結款,我全程保證售后,年輕人的信任感也更強。”李信表示,正是因為他們更好的服務態度和服務流程,他也擁有了一批年輕的回頭客。
對于未來,“收廢品”不只是一個短暫或者糊口的營生,而是楊斌和李信的未來奮斗方向。
楊斌想將自己的“廢品回收”版圖,從青島擴展向全國。
考慮到“父母年齡大了,連微信都不會用”,李信也試圖用自己學到的知識“把家族企業做大做強”,改造“走街串巷”的傳統“吆喝式回收”形式。如今,即便他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在社交平臺更新過,一天也能夠接6-7個電話,“顧客會告訴我需要收什么,我再篩選。”
摸索門道,年入50萬
“收廢品”是一個不起眼卻賺錢的生意。
以自己所在的青島為例,不論規模大小,或者處于上門回收、回收站、回收中心,以及末端工廠的哪個環節,廢品回收確實“收入可觀”。楊斌介紹,“一個廢品回收站一年10萬元保底,好一點能掙20萬元左右,廢品回收中心一年能掙50萬元。”
接棒“收廢品”的第一個月,李信和合伙人定了一個月賺5萬元的“小目標”,最終第一個月他們賺了3萬元,“一個人一萬五千元的純利潤,比我上班要強。”李信也表示。
而原本只是想著簡單過渡一下的阿怡,也能在杭州靠“收廢品”月入過萬元,“其實網點收入主要看位置,由于我們店位置不太好,所以回收價格就便宜一些。”同時,收入浮動也要考慮到天氣因素,“杭州多雨,一旦下雨,就少有生意上門。”
然而,需要注意的是,收廢品的收入高低也與選取的品類大大相關。“比如,雖然搬運銅和紙所需的裝卸、搬運成本不同,但粗略來算,收銅比收紙的收入要高上許多,有的銅一噸能賣到56元一公斤,最高利潤在4000-5000元之間,而且一車就能拉走;但一噸紙,要拉好幾車,才有1000元利潤。”李信介紹。
但其中的臟、累、辛苦,也可想而知。
“每天早上,我7點就起床,干干凈凈地出門,臟兮兮地回家。”阿怡介紹,上門回收沒有節假日一說,每天都是一邊收貨一邊裝貨,一車紙板得裝一兩個小時,“夏天衣服都能擰出水來。”
李信亦表示,雖然利用社交平臺等工具,現在收廢品可以線上下單,輕松了許多,但仍然“很臟、很累”,以裝修為例,不少家庭裝修前總會讓回收公司把窗戶、暖氣片都拆掉,但“有的小區沒電梯,特別沉的空調、老式暖氣片都得徒手搬下來,有時還會被劃傷。”
即使在中游的回收中心,楊斌也免不了辛苦。
最近楊斌接到了一單大生意——為青島的城中村拆遷“善后”,“我們要凌晨兩點半開始干活,天亮前就要全部處理完運回轉運中心。”早上5點天微微亮起時,楊斌已經和員工們結束了一天的大部分工作。
初入行的95后、00后,也免不了踩坑。
“有的顧客從線上下單后,又不肯按照談好的價格出,有時白白折騰人跑一趟,我們也沒辦法。”李信忍不住吐槽道,由于廢品回收這個行業普遍從業者年齡較大,他這么一個“年輕面孔”難免會被顧客刁難。
“有次線上聊好10元一公斤收,結果大熱天過去,顧客說自己10元一斤才出。”價格談不攏要離開的李信,也因為“面嫩”被顧客一頓搶白,“不僅態度惡劣,還說我活該一輩子收廢品。”
同樣踩雷的還有阿怡,剛開始時,阿怡曾覺得“不就是收廢品嗎?有什么難的?”
但實際上接觸后,才發現“收廢品也是有學問的”,由于“年輕沒經驗”,有時阿怡收上來的紙板箱里夾了石子,有時銅線里面摻雜鐵線,有時在易拉罐里塞東西增加重量,“高高興興上門去收,結果去回收站被挑出來,扣了我們的錢。”
初入行的年輕人,也得細心琢磨其中門道,一點一點成長。
“摸爬滾打”之后,阿怡現在回收驗貨更為謹慎,“每一個都檢查,有雜質都挑出來。”到了現在,“有沒有摻假,一看、一拎就知道了。”
“整頓”廢品回收行業
“收廢品”往往是一個“家族生意”,也有“家學淵源”所在。
80年代楊斌的父親就已經走遍青島的大街小巷,回收廢舊金屬等,走街串巷的工具也一路從自行車迭代到貨車,李信的父親也在北京海淀區擁有一畝地的檔口,收銅鋁及稀有金屬類資源,2019年前年收入就達到了50萬元左右。
阿怡則是由在杭州做了多年廢品回收生意的小姨“帶入門”。
但即便年輕人有意,行業有“錢途”,年輕人想從事,或者接棒老一輩的廢品回收生意,除了苦和累,還要克服“職業羞恥感”。
2009年,楊斌大學畢業向父親提出想通過廢品回收創業時,便遭到了極力反對。
在與人進行交流時,阿怡也總說不出口自己是“收廢品的”,更害怕別人異樣的眼光。
變化也在發生。由于父親的反對,大學畢業后楊斌妥協做了十年職業經理人,但楊斌不滿足于“打理別人的生意,我也想擁有自己的事業。”他仍有進行廢品回收創業的計劃,并頻頻向父親提及入行的想法。
“后來社會越來越開放,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狀元,我父親也就想開了。”而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,楊斌從不覺得以自己985雙一流大學的學歷畢業“收廢品”是不光彩的。
李信在大學畢業后選擇“入行”時也并無過多思索和抉擇,“踏實工作沒什么可羞恥的。”
阿怡也在一次和買紙板的阿姨的對話中,掃去了“收廢品”的“職業羞恥感”。
“阿姨和我說,小姑娘辛苦啦,不過你們教大家如何垃圾分類,還回收凈化城市的垃圾,你們在做對這個城市有意義的事情。”阿怡笑著說,“那一刻我被震撼到了,一直以來的自卑被瞬間治愈了。”
楊斌攢著一股勁,決定把所學和廢品回收相結合,改造行業,“我現在就琢磨著,怎么用真正的團隊化運作去改造傳統的廢品回收行業。”楊斌直言,“如果還做傳統模式,那我的大學就真的白讀了。”
未來,他希望能夠基于此前10年職業經理人的工作經歷,把容易踩坑的廢品回收知識細化歸納,“形成培訓課程,幫助95后、00后的小白避雷。”同時,他也在考慮更進一步下沉向終端社區,“去掉中間環節,提高回收效率。”
阿怡也決定把“收廢品”這件有意義的事情堅持下去,而且,“現在收廢品也卷起來了,我們也在不斷嘗試,結合社交平臺讓生意變得越來越好。”
但不可忽視的是,改造“收廢品”行業并非易事。
楊斌直言,即使現在線上小程序已經啟動,但現階段他的客源仍以“線下為主”。
此外,楊斌也提醒,“收廢品”仍然是一門“家族生意”,從業者往往是“親戚帶親戚,朋友帶朋友”,外行人貿然跨行總不免踩坑。
現有的不少打著“互聯網+廢品回收”旗號的公司,技術能力有余,但是對行業的了解卻不足。楊斌表示,同時,當前回收行業,尤其是終端廢品回收站,“不少人建起一個站就開干,等查到再補運營手續,運營不規范也是普遍現象。”
如今,伴隨著年輕人進入廢品回收行業,行業變化和行業新面貌正在展現,“收廢品”也并不意味著不光彩和不體面。“整頓”廢品回收行業,雖路遠任重,但行亦可至。變化,正在發生。